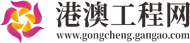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(節錄自台灣大學王世宗教授《東方的意義--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》第三章〈宇宙觀〉) 人生的痛苦不必從感受或事實而來,卻可能由人性直覺而起,易言之生命的悲傷是原罪的作用,故「生年不滿百,常懷千歲憂」(〈古詩十九首〉),人本來就是傷心的,不待外物惹氣;正因此,「怎麼做都不對」是人生的終極感受,諺云「少吃不濟事,多吃濟甚事,有事壞了事,無事生出事」,生命好似為受罪而來。 就健康而言,「大患緣有身,無身則無病」(《蘇文忠公集》〈思無邪齋銘〉),故「身適忘四支」(《白氏長慶集》〈隱几詩〉),而「不知有吾身,此樂最為甚。」(《李太白文集》〈月下獨酌四首〉三) 由此可知,人生之樂常是以吃苦為代價的「苦中作樂」或是「苦盡甘來」,如古人所謂的四大樂事——「久旱逢甘雨、他鄉遇故知、洞房花燭夜、金榜掛名時」(《陔餘叢考》〈成語〉)——所以為樂,其背景皆是長時的受苦,即因苦為本而樂為末,故「平安就是福」,逐歡為樂有其不祥,這使人有時反而畏忌事情如願。 「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,有憂而深憂之者吉」(《春秋繁露》〈玉英〉),承認人生的悲哀竟是減少人生痛苦的要略,於是「誇大」人生不幸的作法成為凡人慣技,如說「天下不如意者恆十居七八」(《晉書》〈羊祜傳〉),這已是可疑,然後人傳說的結果竟成「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」 ,而其質疑者幾無。 在同樣的心理下,「好事不出門,壞事傳千里」與「福無雙至,禍不單行 」皆成為歷久不衰的俗話,這是由於人自身的觀感,而未必為事實,可見憂患意識乃是天賦,故曰「計福勿及,慮禍過之。」(《淮南子》〈人間訓〉)當人生苦多於樂已成常識時,世故老成者莫不知「怒者常情[而]笑者不可測」(李肇《唐國史補》上),「來者不善、善者不來」的機心因此滋生,甚至有感「寧逢惡賓,莫逢故人」(《陔餘叢考》〈成語〉),於是無情的世風使人間更苦,可見惡意是導致凡人悲觀的主因。 人生為苦海,而「海內存知己,天涯如比鄰」(王勃〈杜少府之任蜀州詩〉),仁人君子咸覺「同是天涯淪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識」(《白氏長慶集》〈琵琶行〉) ,故人飢己飢,人溺己溺,視民如傷,而博施濟眾。因為痛苦是普世的而快樂是個別的,所以快樂不能分享而痛苦卻可傳染,「眾或滿堂而飲酒,有人向隅悲泣,則一堂為之不樂」(《韓詩外傳》) ,此乃善意的表現,睹者不覺掃興則必備感欣慰,可見善意使人悲觀,但亦使人少悲而壯,善人與惡人可能同樣悲觀,然其原由必定不同。 「夫人幽苦則思善,故囹圄與福堂同居」(《魏書》〈刑罰志〉七) ,心善者面對人生痛苦時其心更善,因為苦難本是上帝考驗人心的設計,或是好人所以為好人的遭遇。中國士人的道德意識與悲觀態度皆極強烈,這是二者互動互長的結果,同時也是中國文明具有崇高善心的證明,因為悲觀而為善需有堅定的善意,也就是求仁得仁而不計利害的信念。#東方的意義# #中国文明# #宇宙观#
关键词: